- 时间:2018-08-14 20:27:26 来源:58gu.com 作者:
-
《饥饿游戏2:星火燎原》是一部由詹妮弗·劳伦斯、乔什·哈切森和利亚姆·海姆斯沃斯等主演的科幻动作冒险电影,影片剧情精彩,引人入胜,网友们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也是各有不同,一起来看看吧!

01
且不说和CD、英俊一起看的电影,自始至终我都十分喜欢这一系列。凯特尼斯,皮塔,以及他们身边的人,围绕着饥饿游戏进行着服从与抗争的游戏。
电影中11区的老人发出的饥饿鸟的声音,象征性十足。人们不再屈从国会区的统治,人们想要站起来,就像凯特尼斯打破了饥饿游戏的规则。露露,那个小女孩,始终镌刻在凯特尼斯心中,以及读者的心中。
CD联想到了《1984》,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接下来看的书目。
乔安娜的洒脱不羁在电影中刻画得很生动,芬尼克对安妮的情谊没有充分体现。
星火燎原里的凯特尼斯只有在游戏中拿起箭的时候才勇敢无畏。在皮塔失去心跳的时候她会流露女性的软弱,得知皮塔被抓后失去理智也是。人总有不想被人触及的一面,涉及到那一面时,很有可能出现失控的局面。
02
现实主义是一种反动表现模式,它提倡主流意识形态并使其自然化。它使一切都显得很“真实”,而“真实性”是个过程——它使人觉得,意识形态似乎是真实或自然的产物,不是某个特定社会及其文化的产物。——《电视文化》菲斯克
作为《饥饿游戏》系列电影的衍生续集,《饥饿游戏2:星火燎原》在用事实告诉我们,对于有着好口碑、好票房的电影续集,欧美国家对其制作拍摄的重视。这一部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结尾处过于仓促,相比《哈利?波特》系列电影逊色不少,至少“哈利?波特”系列的每一集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一系列的第二部只有让劳伦斯饰演的凯特尼斯被强行注射安眠镇定剂后才强制结束,算影片的弱点之一。
相信常看美剧真人秀的观者看到《饥饿游戏》中的电视噱头定不会觉得陌生,片中电视屏幕上演的感动、悲伤、昂扬、惋惜……种种人情况味,实为每一档“真人秀”节目的标配佐料,就连人物的组合亦然,要有兄妹、有长幼、有万人迷、有怪咖、当然最少不了的是爱情。
“真人秀”(Trueman Show)的流行源自对“真实”的标举,人们渴望探索乃至窥视现实,“真实感”恰因窥视而产生,观者在场的情况下,表演者是在有意识地表演,一旦观者从表演者所在的空间消失,表演者的真正自我总会不知不觉地溢出甚至泛滥。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电视媒体仍然有明目繁多的招术来操纵“真实”,巧妙地拿捏和引导观众的意识,而与其说“真人秀”将银幕上的表演者还原为真人,倒不如说鼓励真人在任何时候都戴上表演的假面。
“一切大众文化都不可避免地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利益服务,因为它不仅为电视制作者与作为消费者的电视观众之间提供了共同点,也为不同观众群体之间提供了共同点,使他们之间的分歧降到了最低限度。这样它就产生了大众艺术作品的常规形态,有效地使观看者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并使他们处于主流意识形态之中。”
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赖以发挥作用的现实主义常规形态的存在,对于确保节目的大众性与可及性是非常必要的,但它们的存在未必就不能给进步的、反对的话语以任何空间。相反,它们提供了能听到反对话语的框架,而它们的反对也构成了戏剧内容的一部分。
与斯巴达克思的揭竿而起不同,凯特尼斯的反抗是从反抗统治者意识形态的符号暴力开始的,从第一部她射穿苹果的行动到在万众瞩目的时刻执起有毒的浆果,再到雪白的婚纱旋转燃烧化为黑色的羽翼,即使手上没有弓箭,她的行为方式便是武器。
这触及了媒介的工具性本质,虽然媒介总会被当权者所利用,但是其本身是中性的,越是精密复杂的媒介工具,越多难以绝对控制的异质性元素。媒介符号的编码与解码不是简单的点对点,权力体制总是试图规定标准化的答案——符合其利益的读解方式,但对抗性的读解始终有生存空间,尤其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严重激化的时刻。
影片打阶级牌的意图非常明显,不需要刻意说明,施惠国与受惠国在空间和人物装束上的差异昭然若揭,摩登都市的纸醉金迷、锦衣华服与煤矿、山林、工厂、衣衫褴褛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会区的统治者希望全民沉迷于“饥饿游戏”真人秀,让施惠国的富人们获得乐趣只是次要目的,更重要的是让受惠国的贫苦大众不知不觉认同实际上对他们不利的意识形态观念,与施惠国的富人和统治者同化,顺从被统治和压迫的命运。通过挑动底层各群体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彼此争斗,掩盖剥削制度的罪恶,转移实质矛盾。
阿尔都塞曾论述“意识形态是人类主体与现实之间的想象性关系”,现实中种种貌似天经地义的秩序与其说是自然规律,不如说是人为了让自己安心生存赋予自然的。《饥饿游戏》系列是一则关于极权、革命以及意识形态魔咒的精巧寓言,位于国会区的施惠国统治者以“真人秀”的娱乐形式向整个国家灌输森严的等级意识,并使之合理化,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逻辑来解释受惠国的悲惨处境,“饥饿游戏”真人秀是这一逻辑的直观表现。表面上游戏中人可以作出种种选择,掌控自身的命运,然而实际上,他们的选择非常有限,被游戏设计者操控于股掌之间,这恰是底层阶级现实生存状况的缩影。片中的媒体网络与古罗马角斗场的功能何其相似?而女主角凯特尼斯便是这个虚构国家的斯巴达克思。
整部影片一直围绕着一个话题进行推进——谁才是你真正的敌人?于是,凯特尼斯被这句话深深地牵引着向前迈进,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原来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将其视为突出重围、结束被贡品生涯的终极人物。剧中“贡品”的死亡,换来的并不是解脱,反而是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的活人杀戮游戏。忍无可忍,无需再忍,身处其中的人物不得不发起反击对抗类似“希特勒”的独裁者总统先生。当凯特尼斯身穿洁白的后现代主义的婚纱出现在众人面前,转身后一生洁白的婚纱被燃烧后成为一只“嘲笑鸟”时,所有人其实早已将其视为反抗独裁统治的领导者,不论是这只成为真正以人身为主体的“嘲笑鸟”,还是每个区的人民举起右手比出的“3”,这都在预示着观众,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反抗即将开始。这就不难解释,这部影片则是一部“过渡电影”,把凯特尼斯与皮塔成功后的短暂的美好生活简要介绍,便立马将他们送回游戏中,起义与反抗到第三部应该才真正开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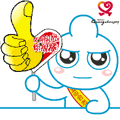
点赞